腓特烈二世 (普鲁士)
| 腓特烈二世 Friedrich II | |
|---|---|
 《腓特烈大帝像》 安顿·格拉夫绘,1781年 | |
| 在普魯士的國王(至1772年) 普魯士國王(1772年之後) 勃兰登堡选侯 | |
| 統治 | 1740年5月31日 – 1786年8月17日(46年78天) |
| 前任 | 腓特烈·威廉一世 |
| 繼任 | 腓特烈·威廉二世 |
| 出生 | 1712年1月24日 |
| 逝世 | 1786年8月17日(74歲) |
| 安葬 | |
| 配偶 | 不倫瑞克-沃爾芬比特爾-貝沃恩的伊麗莎白·克莉絲汀 |
| 王朝 | 霍亨索倫王朝 |
| 父親 | 腓特烈·威廉一世 |
| 母親 | 漢諾威的索菲亞·多蘿西婭 |
| 簽名 |  |
| 普鲁士王家 |
| 霍亨索倫家族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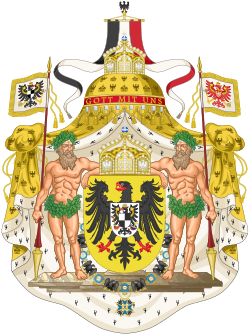 |
| 腓特烈·威廉一世 |
|
| 腓特烈二世 |
腓特烈二世(德語:Friedrich II;1712年1月24日—1786年8月17日),是1740-1786年間在位的普魯士國王。他主要的成就包括西里西亞戰爭中的軍事勝利、對普魯士軍隊的重組、參與對波蘭領土的瓜分,以及對藝術與啟蒙運動的支持。腓特烈是霍亨索倫王朝最後一位被封為「在普魯士的國王」(König in Preußen)的君主,他在吞併皇家普魯士後便開始自稱為「普魯士國王」(König von Preußen)。普魯士在他的統治下成功擴張國土,成為歐洲的軍事大國。腓特烈二世因而被稱腓特烈大帝(德语:Friedrich der Große),抑或其外號老弗里茨(德語:der Alte Fritz)。
腓特烈年輕時對音樂和哲學的興趣高於對兵法的興趣,使其與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發生衝突;但在登上普魯士王位後,他於1742年進攻並併吞了富庶的奧地利西里西亞行省,為自己和普魯士贏得了軍事聲望。他是一位有影響力的軍事理論家,他的分析源於豐富的個人戰場經驗,涵蓋戰略、戰術、機動性和後勤問題。
腓特烈是開明專制的支持者,他說統治者應該是國家的第一僕人。他使普魯士的官僚機構和公務員制度現代化,並在整個王國推行包含從寬容到種族隔離的宗教政策;他改革了司法制度,使平民也有可能成為法官和高級官僚。儘管他對西里西亞和波屬普魯士的天主教徒採取了鎮壓措施,腓特烈仍鼓勵不同國籍和信仰的移民來到普魯士;他支持他喜歡的藝術和哲學家,並允許新聞和文學自由。腓特烈幾乎可以肯定是同性戀,其性取向一直是許多研究的主題。他被安葬在他最喜歡的居所波茨坦的無憂宮。因為他死后无子,他的侄子腓特烈·威廉二世继承王位。
幾乎所有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都將腓特烈塑造成浪漫而伟大的戰士,稱讚他的領導能力、行政效率、忠於職守以及成功地將普魯士打造為歐洲大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後,腓特烈仍是備受尊崇的歷史人物,納粹德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將其稱讚为「偉大的領導人」;二戰後,他的聲望在德國劇烈下降,部分原因是他作為納粹象徵的地位。無論如何,21世紀的歷史學家傾向於將腓特烈視為傑出的軍事領袖和英明的君主,他對啟蒙文化和行政改革的努力為普魯士的崛起以及在與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爭奪德意志地区领导权的斗争中起到了奠基作用。
早年生活
[编辑]腓特烈是時任王儲腓特烈·威廉與漢諾威的索菲亞·多羅特婭的兒子。[1] 他於1712年1月24日晚上11點至12點間出生在柏林宮,並於1月31日由本雅明·烏爾西努斯·馮·貝爾為其施行洗禮,僅取單名「弗里德里希」。[2] 由於他祖父腓特烈一世此前的兩個孫子均早夭,因此這次腓特烈的出生受到了許多歡迎。1713年腓特烈一世去世後,其子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為普魯士國王,使年幼的腓特烈成為王儲。腓特烈共有九位活到成年的兄弟姊妹。他有六位姐妹,其中包括長姊拜羅伊特的威廉明妮,以及烏爾麗卡·埃莉諾拉,後者嫁給瑞典國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並成為瑞典王后。[3] 腓特烈還有三位弟弟,其中包括奧古斯特·威廉與海因里希。[4]

在幼年時期,腓特烈與母親及姊姊維爾赫爾米娜一同生活,[5] 但他們經常前往父親位於科尼斯伍斯特豪森的狩獵行宮。[6] 腓特烈與其長姊建立了親密的關係,[5] 直到她於1758年去世仍然維持。[7] 腓特烈受教育能同時使用法語與德語,[8] 並有許多法國胡格諾派導師。[9] 他的早期教育由蒙巴伊夫人監督,她也曾擔任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教師。他後期的導師,包括語言、古典文學、歷史與修辭學等科目,則是雅克·杜漢·德·讓當與馬蒂蘭·韋西耶爾·拉·克羅茲。[10]
腓特烈·威廉一世因建立龐大的軍隊而被民間稱為「士兵國王」,其中包含著名的「波茨坦巨人衛隊」部隊;他嚴格管理王國財政,並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他性情暴躁,以絕對權威統治勃蘭登堡-普魯士。[11] 相對而言,腓特烈的母親索菲亞則舉止優雅、富有魅力且學識淵博。她的父親布倫瑞克-呂訥堡的格奧爾格·路德維希於1714年繼承大不列顛王位,成為喬治一世。[12] 父母之間在政治與個人上的差異,[13] 對腓特烈的文化觀、君主角色以及他與父親的關係產生了深遠影響。[5]
儘管父親希望他的教育完全偏向宗教與實用主義,年輕的腓特烈仍發展出對音樂、文學與法國文化的興趣。腓特烈·威廉認為這些愛好過於柔弱,[14] 與其軍國主義背道而馳,因而經常對腓特烈施以鞭打與羞辱。[15] 然而,腓特烈在導師杜漢的幫助下,秘密建立了一個藏書達三千冊的圖書館,收藏詩歌、古希臘與古羅馬的經典作品,以及哲學著作,以補充其官方課程。[16]
腓特烈·威廉一世雖然生於路德宗信仰的普魯士,但卻在加爾文宗傳統下成長;他擔心自己並非上帝的無條件選召之一。為避免兒子腓特烈陷入同樣的疑慮,國王下令不得向其教授預定論。然而,儘管父親的禁令,腓特烈似乎仍然為自己採納了一種宿命觀。[17]
王太子
[编辑]卡特事件
[编辑]
在其18歲的時候,腓特烈與比他年長8歲的普魯士軍官漢斯·赫爾曼·馮·卡特(Hans Hermann von Katte,1704-1730)成為了親密好友,卡特成為了腓特烈的摯友之一,甚至可能是他的情人。[18] 在英國婚姻計劃破滅後,腓特烈與卡特及其他低階軍官密謀逃往英國。[19] 當王室隨從隊伍行至普法爾茨選侯國的曼海姆附近時,彼得·基思的兄弟、同為腓特烈同伴的羅伯特·基思在陰謀即將展開之際良心不安,於1730年8月5日向腓特烈·威廉請求寬恕。[20] 隨後腓特烈與卡特被捕,並囚禁於屈斯特林。由於兩人身為軍官卻企圖逃離普魯士前往英國,腓特烈·威廉以叛國罪指控他們。國王一度威脅要處死王儲,甚至考慮迫使腓特烈放棄繼承權,轉由其弟奧古斯特·威廉繼承,儘管這兩種選項都難以向神聖羅馬帝國議會交代。[21] 最終國王判處卡特死刑,並強迫腓特烈在1730年11月6日於克斯特林親眼目睹他的斬首;王儲在致命一擊前不久暈倒。[22]
腓特烈於1730年11月18日獲得赦免並釋放,但被剝奪軍銜。[23] 他被迫留在克斯特林,並開始在戰爭及財政部門接受嚴格的治國與行政訓練。次年腓特烈·威廉前往克斯特林探訪,父子間的緊張關係稍微緩解,腓特烈獲准於1731年11月20日前往柏林,參加姐姐維爾赫爾米娜與拜羅伊特藩侯腓特烈的婚禮。[24] 在1732年2月26日,腓特烈最終結束於克斯特林的「管教期」並返回柏林,條件是他必須與不倫瑞克-貝弗恩的伊莉莎白·克里斯汀結婚。[25]
腓特烈在他的父親「士兵國王」腓特烈·威廉一世嚴格和軍事式的教育下長大。受其母亲影响,其喜好文学艺术和法国文化,并一再与鄙视法國文艺的父王发生冲突。1730年,为反抗其父强加的婚姻,他嘗試和朋友漢斯·赫爾曼·馮·卡特逃往英国,但以失敗告終。他們被囚禁在現在屈斯特林,隨後國王殺死了卡特。
大多数现代传记作家认为腓特烈幾乎是百分之百同性恋,且他的性傾向对其生活和性格起到至关重要作用[26][27][28][29][30]。
转变与成熟
[编辑]
1732年,腓特烈被恢復普魯士軍職,擔任戈爾茨團上校,駐紮於瑙恩與諾伊魯平附近。[31] 當普魯士在波蘭王位繼承戰爭中向神聖羅馬帝國軍隊派遣部隊支援時,腓特烈在薩伏依的歐根親王麾下參與對法國的萊茵河戰役;[32] 他觀察到歐根指揮下的神聖羅馬帝國軍隊孱弱,並在登基後藉此對奧地利加以利用。[33] 患有痛風且意欲和解的腓特烈·威廉將位於萊因斯貝格(諾伊魯平以北)的萊因斯貝格宮賜予腓特烈。腓特烈在此集結音樂家、演員及其他藝術家,閱讀、觀賞與出演戲劇,並創作與演奏音樂。[34] 他還與友人組建「巴亞爾勳位」(Bayard Order)以討論軍事,並推舉海因里希·奧古斯特·德·拉·莫特·富凱為聚會的大師。[35] 腓特烈後來將這段時光視為其一生中最幸福的歲月之一。[36]
研讀尼科洛·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如《君主論》)被視為歐洲君主有效統治的必要準備。1739年,腓特烈完成了《反馬基雅維利》,這是一部對馬基雅維利的理想主義式反駁。該書以法語撰寫——腓特烈的所有著作皆用法語——並於1740年匿名出版,但由伏爾泰在阿姆斯特丹發行,廣受歡迎。[37] 腓特烈致力於藝術而非政治的歲月隨著1740年腓特烈·威廉去世、腓特烈繼承普魯士王國而結束。父子二人在後者臨終時和解,腓特烈後來承認,儘管兩人長期衝突,腓特烈·威廉仍是一位有效的統治者:「他是多麼可怕的人。但他公正、聰明,且擅長政務……正是憑藉他的努力與不懈勞動,我才能完成此後的一切事業。」[38]
婚姻
[编辑]隨著國王一再受到親奧勢力(如克魯姆科夫(Friedrich Wilhelm von Grumbkow)、古恩德林(Jacob Paul von Gundling)等人)的壓力,腓特烈在其影響下,不情願和伊麗莎白·克莉絲汀成婚,后者是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皇后(查理六世皇帝的妻子)堂妹,这次婚姻使得腓特烈与查理六世,帝俄的皇储阿列克谢(彼得一世长子)成为连襟。婚后兩人感情不睦,並未诞下任何子女。腓特烈基本上和她分居,只在節慶場合一同出現。但腓特烈在其父臨終前,答應不會對伊麗莎白不忠。在萊茵斯貝格的四年(1736–1740)可能是這對伉儷最幸福的日子。但這究竟是真的,還是只是做給他那多疑父親的一齣戲,目前尚沒有定論。
腓特烈同時和彼得·卡尔·克里斯托弗·冯·克斯(Peter Karl Christoph von Keith)和汉斯·卡尔·冯·温特菲尔德(Hans Karl von Winterfeldt)有著親密的友誼。他對女性比較疏遠,希望在女性身上也看到他在男性那裡看到的勃勃生機。在他身後作的屍檢並未發現他患有性病或畸形。因爲他的醫生约翰·格奥尔格·齐默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透露,腓特烈大婚之前曾經感染性病。難得幾位受腓特烈青睞的女性,都是些所謂的“女大地主”如葉卡捷琳娜大帝,他還给她們寫過詩,保持書信來往。
統治
[编辑]順位登基
[编辑]

腓特烈在1740年6月1日(其父逝世的翌日)登基,年方28歲。[39] 腓特烈·威廉一世為他留下了一個高度軍事化的國家。當時普魯士在人口上居歐洲第十二位,但其軍隊規模則排名第四,僅次於法國、俄羅斯與奧地利。[40] 在普魯士,平均每28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士兵,而在英國則是每310人中才有一名士兵;軍事開銷佔普魯士國家預算的86%。[41] 在腓特烈繼位時,由腓特烈·威廉一世訓練出的普魯士步兵,在紀律與火力方面幾乎無可匹敵。至1770年,腓特烈將他繼承的龐大軍隊規模翻了一倍。1786年,米拉波侯爵的名言總結了這一局勢:「普魯士不是擁有軍隊的國家,而是擁有國家的軍隊」(「La Prusse n'est pas un pays qui a une armée, c'est une armée qui a un pays」)。[42][43] 憑藉其節儉父親積累的資源,腓特烈最終成功將普魯士建立為歐洲第五個、也是最小的一個列強。[44]
當腓特烈於1740年繼位,成為第三任「普魯士國王」時,他的領土由分散各地的區域組成,包括位於神聖羅馬帝國西部的克萊沃、馬克和拉文斯貝格;帝國東部的勃蘭登堡、前波美拉尼亞與後波美拉尼亞;以及位於帝國之外、與波蘭立陶宛聯邦接壤的普魯士王國(原普魯士公國)。[45]
東南用兵
[编辑]
受法國啟蒙哲學思想薰陶的腓特烈二世甫一繼位,就被當時人們認為將是一位善於思考、敢于打破专制统治的開明國王,甚至可能偏於文弱。的確,他一上臺就解散父親的普魯士巨人擲彈兵團(留一個中隊作儀仗護衛),而且下令禁止軍中體罰士兵(這個命令後來在戰爭中撤銷),同时采取开放言论自由、分派粮食给市民、禁止刑讯的措施。但腓特烈擁有祖、父遺留下來的精良軍隊和充足國庫,本人對戰爭也不是生手。最重要的是,腓特烈登基不久就出現普魯士擴張的良機——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其立即打破人们的固有印象,积极发动并参加战争。
1739年,奧地利帝國方才結束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戰爭,所產生的外交破綻剛好爲普魯士利用。透過這場戰爭,自然資源匱乏的普魯士贏得極具經濟價值的西里西亞地區,同時爲普魯士賺得一條易守難攻的邊界線。在這次戰爭,腓特烈二世和陸軍元帥库尔特·克里斯托夫·冯·施维林伯爵爲普魯士贏得西里西亞。在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中,他成功保衛該地;普魯士並沒有全程參與這場戰爭,只打一前一後兩段,全都是為吞併奧地利的西里西亞省,對於普魯士來說,就稱為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和第二次西里西亞戰爭,所以這兩場戰爭實際都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中的一部分。同時在這場戰爭中,腓特烈初次親身領軍,在幾次戰役中展露他的軍事才華。
儘管奧地利王位繼承戰到1748年才正式結束,腓特烈的普魯士王國卻從1745年就退出戰爭,作壁上觀;從此到1756年七年戰爭爆發前,腓特烈贏得十年的和平建設時期。西里西亞是紡織工業中心,德意志最為富庶的省份之一,每年稅收要占整個普魯士稅入的1/4。在這十年裡腓特烈整軍經武,發展經濟,為後來的七年戰爭作好準備。
七年戰爭
[编辑]1750年代普魯士的外交形勢越來越嚴峻。首先腓特烈與英國交好,於1756年締結《西敏條約》(Treaty of Westminster),保證英王在德意志的漢諾威領土不受侵犯,並以武力「對付侵犯德意志領土完整的任何國家」,大大觸怒與英國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法國。而奧地利女皇瑪麗婭·特蕾西婭和她的首相考尼次成功聯合俄國女沙皇伊莉莎白·彼得羅芙娜和法王路易十五(史學家將法奧結盟稱為外交革命),漸漸給普魯士的脖子套上外交絞索,積極準備收復西里西亞。
1756年腓特烈看到形勢日益嚴重,決定與其坐等戰爭降臨,不如對奧地利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七年戰爭由此展開。他的部隊首先打進在這場紛爭中與奧地利結盟的薩克森選侯國,之後普魯士同時和兩個鄰邦大國,即奧地利和俄羅斯帝國作戰。經過7年大戰,幾次面臨亡國邊緣,腓特烈終於因為勃蘭登堡王室的奇蹟才保住西里西亞;他個人也成為軍事史上的名將,贏得「大帝」的稱號,更樹立「軍事天才」的個人榮譽。在伏爾泰和米拉波等人的見證下,普魯士在这群雄爭霸年代成為列強,一躍成爲歐洲第五大強國。
瓜分波蘭
[编辑]腓特烈企圖獲得並經濟性地利用波蘭普魯士,作為其富國目標的一部分。[46] 早在1731年,腓特烈就曾表示其國家可因併吞波蘭領土而受益,[47] 並將波蘭比喻為「朝鮮薊,可一片片地被吞食」。[48] 到1752年,他已為瓜分波蘭-立陶宛做好鋪墊,目標是建立一條連接波美拉尼亞、勃蘭登堡與東普魯士的領土走廊。[49] 新獲得的領土將增加稅收基礎,為軍隊提供人力,並充當其他列強海外殖民地的替代品。[50]
由於治理不善與外國勢力干預,波蘭易於遭受瓜分。[51] 腓特烈本人亦須為此衰弱負責,因為他反對波蘭的財政與政治改革,[46] 並利用波蘭的鑄幣模具大量鑄幣,導致其貨幣貶值。其收益超過2,500萬塔勒,相當於普魯士和平時期國家預算的兩倍。[52] 他還在維斯瓦河畔的馬林韋爾德建立海關要塞,阻撓波蘭建立穩定經濟體系,[46] 並炮擊維斯瓦河上的波蘭海關港口。[53]
腓特烈還利用波蘭的宗教分歧,使其更易受普魯士控制。[54] 波蘭主要信奉羅馬天主教,但約有10%人口屬於異端:包括60萬東正教徒與25萬新教徒。到了1760年代,這些異端的政治重要性遠超其人口比例。雖然異端仍享有相當的權利,但在一段宗教與政治自由的時期後,波蘭-立陶宛聯邦逐漸削減其公民權。[55] 不久後,新教徒被禁止進入公職與瑟姆(波蘭議會)。[56] 腓特烈利用此局勢,自詡為波蘭新教利益的保護者,以宗教自由之名推動普魯士的影響力。[57] 他進一步透過與葉卡捷琳娜二世結盟打開普魯士的控制之路,後者將其舊情人與寵臣斯坦尼斯瓦夫·奧古斯特·波尼亞托夫斯基推上波蘭王位。[58]

1769年至1770年間,俄國佔領了多瑙河公國,腓特烈的弟弟亨利親王作為駐聖彼得堡代表,說服腓特烈與瑪麗亞·特蕾西婭,認為與其讓俄國從鄂圖曼獲取領土,不如三方共同瓜分波蘭-立陶宛聯邦以維持權力平衡。於是1772年三方同意進行波蘭的第一次瓜分,且未爆發戰爭。腓特烈獲得大部分皇家普魯士,併吞了38,000平方公里(15,000平方英里)土地與60萬居民。雖然普魯士所分得的面積最小,但其經濟價值大致與其他列強相當,且具有重大戰略意義。[59] 新設的西普魯士省份連接了東普魯士與後波美拉尼亞,賦予普魯士控制維斯瓦河河口的權力,並切斷波蘭的海上貿易。瑪麗亞·特蕾西婭雖然極不情願地同意瓜分,但腓特烈挖苦地評論說:「她一邊哭泣,一邊接受。」[60]
腓特烈打著「開明文明使命」的旗號,對波蘭領土進行開發,強調普魯士方式的文化優越性。[61] 他將波蘭普魯士視為野蠻未開化之地,[62] 並稱其居民為「邋遢的波蘭渣滓」。[63] 他的長期目標是透過德意志化來清除波蘭人,包括沒收波蘭王室領地與修道院財產、[64] 實行徵兵制、鼓勵德國人遷入該地,以及推行嚴重加重波蘭貴族負擔的稅收政策。[65]
1772年,奧地利和1764年新近與普魯士結盟的俄羅斯處於武裝衝突邊緣,腓特烈二世爲自身利益,倡導瓜分波兰,用波蘭去滿足兩國對土地的欲望;普魯士武力兼併所謂的波蘭-普魯士,即是西普魯士。從此他自稱爲腓特烈二世,为普魯士國王(König von Preußen),而不是像其兩屆前任,稱自己爲在普魯士的國王(König in Preußen)。
巴伐利亞
[编辑]
在晚年,腓特烈於1778年將普魯士捲入小規模的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他阻止了奧地利試圖以奧屬尼德蘭交換巴伐利亞的企圖。[66] 奧地利方面則試圖向法國施壓以參戰,理由是涉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保證條款,該條款將法國的波旁王朝與奧地利的哈布斯堡-洛林王朝聯繫在一起。然而對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而言不幸的是,法國宮廷並不願支持他,因為法國已經在北美支援美洲革命者,而且自七年戰爭結束以來,與奧地利結盟的想法在法國一直不受歡迎。[67] 結果奧地利幾乎被孤立,腓特烈反而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受益者。[68]
薩克森與俄羅斯在七年戰爭時曾是奧地利的盟友,這時卻與普魯士結盟。[69] 雖然腓特烈在晚年對戰爭感到厭倦,但他仍決心不讓奧地利在德意志事務中佔據主導地位。[70] 腓特烈與亨利親王率普軍進入波希米亞迎戰約瑟夫的軍隊,但雙方最終陷入僵局,主要依靠就地取材維持並不斷發生小規模衝突。[71] 腓特烈的宿敵瑪麗亞·特蕾西婭——約瑟夫的母親及共治者——不願與普魯士再戰,於是秘密派使者與腓特烈討論和談。[72] 最後俄羅斯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威脅若不和談便出兵支援腓特烈,迫使約瑟夫不情願地放棄對巴伐利亞的主張。[73] 當約瑟夫於1784年再度圖謀時,腓特烈建立了諸侯聯盟(Fürstenbund),使自己成為「德意志自由的捍衛者」。為了阻止約瑟夫二世併吞巴伐利亞,腓特烈爭取到漢諾威與薩克森選侯,以及若干小邦親王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德意志教會的高級教長——美因茨大主教,同時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總理官——投向腓特烈,進一步強化了普魯士在德意志邦國中的地位。[74]
內政改革
[编辑]在內政方面,他推行農業改革(馬鈴薯)、軍事改革、教育改革、法律改革,在德羅姆林(Drömling)和奧得沼澤實施排水工程,廢除刑訊,還建立廉潔高效的公務員制度。他對法律的發展貢獻良多。另外,當時普魯士的人民可以通過上書或求見的方式向國王求助。
腓特烈二世的名言是“國王是國家的公僕”,在該準則下,他竭力避免封建制度的流弊;對此,他對自己手下的官員非常不信任,他深深感到等級觀念會作祟。
| “ | 我很不高興,那些在柏林吃上官司的窮人,處境是如此艱難。還有他們動輒就會被拘捕,比如來自東普魯士的雅各·特雷赫,他因爲一場官司而要在柏林逗留,警察就將他逮捕,後來我讓警察釋放他。我想清楚告訴你們,在我的眼中,一個窮困農民和一個最顯赫公爵或一個最富裕貴族沒有絲毫高低之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 |
腓特烈二世“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是他當政時期的特色,他對少數民族移民和少數宗教信徒(如胡格諾派信徒,天主教信徒)采取寬容開放政策,鼓励宗教自由;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克花園(Forum Fridericianum)裡,一座新教教堂和一座天主教教堂並排而立,在18世紀時可算得上是獨一無二的景致。腓特烈甚至说过如果土耳其人到柏林定居,可为他们修建清真寺,後來還說:「縱然各行各路,但人人都有機會升上天國!」(“Jeder soll nach seiner Façon selig werden”)。但對猶太人,腓特烈二世卻一字不漏繼承其前任各君王的政策,一面歧視,一面利用:一方面欢迎犹太人移居普鲁士,甚至建立犹太区安置他们,并资助犹太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摩西·门德尔松活动;另一方面又颁布种种严格法令规管,如1750年修訂後的總特權条例(Revidiertes General-Privileg)及1763年的猶太瓷器法规(Judenporzellanverordnung)。另外,普魯士是歐洲第一個享有有限出版自由的君主國。

腓特烈二世希望徹底廢除農奴制,但在地主的強烈反對下失敗,仅在國王的屬地上逐步實行,腓特烈二世在新開闢的地區裡建立小鎮和農村,讓有自由身份的農民入住。當出於國務原因而需要延長農奴合同的時候,這些幫工、雇農和女僕會被問情況及待遇,腓特烈二世會把受到不公待遇的雇農改屬到管理有方的地主。
在腓特烈二世統治時期,延续其父的教育政策,普魯士興建數以百計的學校。但鄉村學校为普鲁士军事扩张服务,其師資来源多为退伍军人,素質良莠不齊,只能培養出具有讀寫能力(非文盲)的国民。但无论如何,腓特烈二世掃盲有極大的成就,普鲁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全民教育的国家(1763年)。
腓特烈二世和伏爾泰有書信來往,並且曾經在波茨坦會面過;他自己寫有大量法文著作,可說是18世紀影響很大的一位作家。他於1740年寫下的《反馬基維利》在歐洲非常有名,他用進步角度去批判馬基維利充滿權術角度的《君王論》(但事實上腓特烈並不見得不用權術)。廣爲流傳的無憂宮磨坊主傳說被視爲腓特烈二世對法律一次較量,事實上磨坊主富格爾(Vogel)確實因此起诉国王,国王给予其权利并从1781年豁免他的租金。但此後該磨坊因為倒塌而被拆除,今天所謂歷史上的無憂宮磨坊,其實是由荷蘭移民家族范登博斯(van der Bosch)——修建的一座三層顶楼荷兰式风磨。在威廉一世(1871年成为德国皇帝)1861年成为普鲁士国王时,他宣布该磨坊成为纪念物,并且作为免费参观的博物馆。1883年一个机翼出现损坏,结果整个风车被更换一新。
腓特烈当政时期,普鲁士各方面人才开始陆续出现,如洪堡兄弟、施泰因、哈登貝格等,为普鲁士19世纪初的改革奠定人才基础。
在腓特烈二世的晚年,雖然內政與經濟都因為他的勤奮治理而蒸蒸日上,但人民卻失去對國王的愛戴;人民雖然畏懼這位戰場英雄,卻背地裡嘲笑他是個「終日磨麥」的老頭。人民承受極端的沈重稅負而苦悶不已(連賣藝討生活的街頭藝人也被課稅),重稅讓腓特烈二世保有強大的常備軍(16萬人),同時也使他大失民心;一位英國大使曾經對腓特烈晚年的新稅制評論說:「新的抽稅方法不只抽走人民的金錢,實際上更抽走人民對國王的感情」。[75]
宗教信仰
[编辑]
與虔誠的加爾文宗父親不同,腓特烈是一位宗教懷疑論者,常被描述為自然神論者。[77][a] 然而,腓特烈在宗教信仰上相當務實。他一生三度公開表達基督徒信仰:1730年卡特被處決後他被囚時、1741年征服西里西亞後,以及1756年七年戰爭爆發前夕。每一次的信仰表白同時也具有個人或政治目的。[80]
他在國內容忍各種信仰,但新教仍為優待宗教,天主教徒則未被選入高級官職。[81] 腓特烈期望全國發展,並依各地需要而調整。他有意吸引多元技能人才,不論是耶穌會教師、胡格諾派市民,或是猶太商人與銀行家。腓特烈保留耶穌會士在西里西亞、瓦爾米亞及內茲區擔任教師,認可其教育活動對國家的貢獻。[82] 在教宗克勉十四世取締耶穌會後,他仍繼續支持他們。[83] 他還與瓦爾米亞親王主教伊格納齊·克拉西茨基交好,並邀請他於1773年祝聖聖海德維希座堂。[84] 他接納無數來自波希米亞的清教織工,這些人因逃避虔誠的天主教徒瑪麗亞·特蕾西婭的統治而遷入,並給予他們免稅與免服兵役的待遇。[85] 他不斷尋找新殖民者,強調民族與宗教與他無關。這一政策使普魯士人口在腓特烈三場戰爭造成重大損失後能迅速恢復。[86]
雖然腓特烈被認為比許多鄰近德意志邦國更能容忍猶太人和天主教徒,但他的實用寬容並非毫無偏見。他在《政治遺囑》中寫道:
我們城鎮裡猶太人太多了。他們在波蘭邊境是必要的,因為那裡只有猶太人從事商業活動。但一旦遠離邊境,猶太人就成為累贅,他們結黨營私,走私違禁品,並幹盡各種對基督徒市民和商人有害的勾當。我從未因這或任何教派而迫害任何人;不過,我認為謹慎起見,應防止他們的人數繼續增加。[87]
在佔領領土上,腓特烈對天主教的寬容度則低得多。在西里西亞,他無視天主教會法典,安插對他忠誠的神職人員。[88] 在波蘭普魯士,他沒收天主教會的財產,[64] 使神職人員依賴政府的薪俸,並規定其職務內容。[89]
與許多啟蒙時代領袖一樣,腓特烈亦為一名共濟會成員,[90] 他於1738年赴不倫瑞克旅行時加入。[91] 他的入會使該團體在普魯士獲得合法地位,並免於被控顛覆活動。[92] 1786年,他成為第33級最高會議的首任大總司令,其使用的雙頭鷹徽章後來成為32級與33級共濟會員的標誌,隨著七個新等級加入共濟會儀式而確立。[93]
腓特烈的宗教觀點最終受到反革命的法國耶穌會士奧古斯丁·巴呂埃爾的譴責。在1797年的《雅各賓主義史回憶錄》中,巴呂埃爾闡述了一個有影響力的陰謀論,指控腓特烈與伏爾泰、達朗貝爾、丹尼斯·狄德羅等人一同密謀,企圖「摧毀基督教」並煽動「對國王與君主的叛亂」,而腓特烈則是他們的秘密「保護者與顧問」。[94]
逝世
[编辑]1786年8月17日,腓特烈二世于無憂宮中在他的沙發椅上安詳辭世,享壽74歲;他身後無子,由侄子繼承,即腓特烈·威廉二世,此時距離法國大革命僅有3年。他的意願是葬在無憂宮露臺他的愛犬旁,但他的繼任,也是他的侄子卻將他葬在波茨坦驻军教堂(德語:Garnisonkirche)地下墓室裡。1944年他的棺材被移往馬尔堡的伊麗莎白教堂,直到1952年,才在路易·斐迪南的發起下被遷到霍亨索倫城堡;但直到兩德統一後的1991年8月17日,這位國王才到他想到的地方,在他生前已經建好的墓穴下安身。他的話:「吾到彼處,方吿無憂。」(法語:Quand je suis là, je suis sans souci.)這位思想自由的共濟會員在教堂裡尋不得安寧,願意離自己的愛犬更近一些。
人們在瓦爾哈拉神殿爲他塑半身像以作紀念。在他過身後,人們樹立很多紀念碑,最有名的是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腓特烈大帝騎馬像;二戰時塑像幸存,並在東德時期重建。
评价
[编辑]軍事天才
[编辑]




即使忽略腓特烈作爲政治家的作爲和對立法所做的貢獻,單憑在軍事上的表現,就足以使他在歷史上占一席位。在西方軍事歷史學家的著作中,腓特烈在歷代名將中的地位,可謂是十分輝煌;拿破崙認為其在近代歐洲軍事史的地位,僅次於蒂雷納子爵與古斯塔夫·阿道夫等人。[95]
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腓特烈初次綻放光芒。索爾戰役更是腓特烈第一次試圖把經過自己思考和設計的斜線式戰術付諸實施。戰後腓特烈寫出他最重要的軍事理論著作《戰爭原理》(有譯為軍事教令,德語:Die General Principia vom Kriege)。這本書集中體現腓特烈對自己早期戰爭經驗的總結和思考,不僅僅是形而上的戰爭理論,而且貼近現實,是當時最好的戰爭實踐指南。腓特烈其實是用法文寫成此書的,後來才譯成德文,僅僅下發給普魯士的將級軍官,不得外傳;但他沒有把法文原版的第12章翻成德文,因為這一章寫的是腓特烈本人駕馭部下經驗,當然不願意讓部下看見。後來在七年戰爭中的1760年2月,奧地利從一位被俘虜的普魯士少將那裡得到此書,這才流傳於世,1762年傳到倫敦,在那裡公開刻印出版。
七年戰爭中,腓特烈大帝愈挫愈強,以驚人的毅力和頑強以普魯士一個小國之力獨抗俄、奧兩大強國。羅斯巴赫會戰更是腓特烈斜線陣勢完美的表演之一,今天被美國西點軍校選作那個時代的經典戰役,以大模型重現在它的軍事博物館陳列中。軍事史家亦把此戰與洛伊滕會戰許為腓特烈大帝軍事藝術的巔峰之作,就像拿破崙的奧斯特里茨會戰一樣;僅憑這兩場會戰,腓特烈就完全奠定其作為近代最偉大名將之一的地位。後世拿破崙評價腓特烈大帝的時候說:「越是在最危急的時候,就越顯得他的偉大,這是我們對於他能說的最高讚譽之詞」。
1785年西里西亞一年一度的秋季大演習中,英國王弟腓特烈王子、美國獨立戰爭中出名的康沃里斯將軍、拉法葉特侯爵都來參觀,並向腓特烈致敬。當時腓特烈指揮的普魯士軍隊操演方法成為全歐洲軍界競相模仿樣板。
藝術造詣
[编辑]
他對所有藝術都感興趣,他自己起草設計波茨坦的無憂宮,並聘請建築師克諾伯斯多夫興建。他收有很多名畫,吹得一口好長笛(長笛教師約翰·約阿希姆·匡茨(Johann Joachim Quantz)),同时还能够进行作曲。他於1747年在無憂宮與作曲家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會面。
除了母語德語,腓特烈二世還能說法語、英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他也能聽懂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希臘語,還有希伯來語。他晚年的時候,還去學習斯拉夫語與巴斯克語。
後世纪念
[编辑]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对腓特烈二世有很高评价,认为是他将普鲁士打造成欧洲强国。直到二战前,德国人都始终十分崇拜他,不少纳粹党人认为他是可以与希特勒比肩的伟大领导人,而希特勒本人也十分崇拜腓特烈二世。二战后,由于成为纳粹的标志,腓特烈二世的地位受到削弱。在2003年舉辦最偉大的德國人票選中,他排名第42。
2012年是腓特烈二世诞辰300周年,无忧宫、德國历史博物馆等地将举办一系列展览以纪念。同时,其生日的1月24日晚,柏林举办腓特烈主题音乐会,時任德国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出席并致辞。出版业界也推出一系列有关腓特烈的书籍,其中包括收錄其生平的《腓特烈辞典》。
家谱
[编辑]| 腓特烈·威廉 勃蘭登堡選侯 | 拿騷的路易絲·亨麗埃特 | 恩斯特·奧古斯特 汉诺威选侯 | 索菲娅 汉诺威选侯夫人 | 格奧爾格·威廉 | 伊利諾·達美婭·杜布斯 | ||||||||||||||||||||||||||||||||||||||||||||||
| 腓特烈一世 勃蘭登堡選侯、普鲁士國王 | 索菲亞·夏洛特 普鲁士王后 | 乔治一世 大不列顛國王 | 索菲亞·多魯西亞 | ||||||||||||||||||||||||||||||||||||||||||||||||
| 腓特烈·威廉一世 勃蘭登堡選侯、普鲁士國王 | 索菲·多羅特婭 普鲁士王后 | ||||||||||||||||||||||||||||||||||||||||||||||||||
| 腓特烈二世 | |||||||||||||||||||||||||||||||||||||||||||||||||||
参见
[编辑]註釋
[编辑]- ^ Schieder 1983,第1頁.
- ^ MacDonogh 2000,第28頁.
- ^ Asprey 1986,第277頁.
- ^ Schieder 1983,第39頁.
- ^ 5.0 5.1 5.2 Lavisse 1892,第128–220頁.
- ^ Kugler 1840,第54–55頁; Mitford 1970,第28–29頁; Schieder 1983,第7頁.
- ^ Christian 1888,第11–12頁.
- ^ Asprey 1986,第[ https://archive.org/details/frederickgreatma00aspr/page/n46 17]頁.
- ^ Lavisse, 1892 & [https://archive.org/details/youthoffrederick0000lavi/page/9–11].
- ^ Lavisse 1892,第9頁.
- ^ Asprey 1986,第14–15頁; MacDonogh 2000,第16–17頁.
- ^ Kugler 1840,第20–21頁.
- ^ Fraser 2001,第12–13頁; Ritter 1936,第24–25頁.
- ^ MacDonogh 2000,第47頁; Mitford 1970,第19頁; Showalter 1986,第xiv頁.
- ^ Kugler 1840,第39–38頁; MacDonogh 2000,第47頁; Ritter 1936,第26–27頁.
- ^ MacDonogh 2000,第37頁.
- ^ Fraser 2001,第58頁; MacDonogh 2000,第35頁; Ritter 1936,第54頁.
- ^ Asprey 1986,第51–53頁; Blanning 2015,3:55–4:56; Simon 1963,第76頁; Mitford 1970,第61頁.
- ^ de Catt 1884,第60–61頁.
- ^ MacDonogh 2000,第63頁.
- ^ Reiners 1960,第41頁.
- ^ Mitford 1970,第61頁.
- ^ Reiners 1960,第52頁.
- ^ Kugler 1840,第94頁.
- ^ Asprey 1986,第88–89頁; MacDonogh 2000,第86–89頁.
- ^ Reinhard Alings, "Don't ask – don't tell: War Friedrich schwul?" In Friederisiko: Friedrich der Große: Die Ausstellung (Munich: Hirmer, 2012), pp. 238-247.
- ^ Blanning 2016,第55–56, 77頁.
- ^ Wolfgang Burgdorf, Friedrich der Große (Freiburg: Herder 2011), pp. 67ff.
- ^ Peter-Michael Hahn, 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Feldherr, Autokrat und Selbstdarsteller (Stuttgart: W. Kohlhammer 2013), chapter 2.
- ^ Susan W. Henderson,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A Homophile Perspective", Gai Saber 1, no. 1 (1977), pp. 46-54.
- ^ Kugler 1840,第96頁.
- ^ Kugler 1840,第108–113頁.
- ^ Reiners 1960,第71頁.
- ^ Kugler 1840,第122頁.
- ^ Kugler 1840,第123頁.
- ^ Hamilton 1880,第316頁.
- ^ MacDonogh 2000,第125頁.
- ^ Duffy 1985,第20頁.
- ^ Luvaas 1966,第3頁.
- ^ Ergang 1941,第38頁.
- ^ Sontheimer 2016,第106–107頁: Bei der Thronbesteigung von Friedrich II. kam in Preußen auf 28 Bewohner ein Soldat, in Großbritannien auf 310. Da Preußen nur 2,24 Millionen Bewohner hatte, war die Armee mit 80000 Mann noch relativ klein, verschlang aber 86 Prozent des Staatshaushalts. [腓特烈二世登基時,普魯士每28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士兵,而英國則是每310人。由於普魯士僅有224萬居民,8萬人的軍隊規模仍算相對小,但卻吞噬了國家預算的86%。]
- ^ Baron 2015.
- ^ Billows 1995,第17頁.
- ^ Longman 1899,第19頁.
- ^ Kugler 1840,第544–545頁.
- ^ 46.0 46.1 46.2 Scott 2001,第176頁.
- ^ MacDonogh 2000,第78頁.
- ^ Clark 2006,第231頁.
- ^ Friedrich 2000,第189頁.
- ^ Hagen 1976,第118–119頁.
- ^ Konopczyński 1919,第28–33頁.
- ^ Lukowski 2013,第176頁.
- ^ Davies 1996,第663頁.
- ^ Konopczyński 1919,第34頁.
- ^ Scott 2001,第177頁.
- ^ Teter 2005,第57–58頁.
- ^ Scott 2001,第177–178頁.
- ^ Hodgetts 1914,第228–230頁.
- ^ Kaplan 1962,第188–189頁.
- ^ Ritter 1936,第192頁.
- ^ Clark 2006,第239頁.
- ^ Egremont 2011,第36頁.
- ^ Kakel 2013,第213頁.
- ^ 64.0 64.1 Konopczyński 1919,第46頁.
- ^ Hagen 1976,第119頁.
- ^ Stollberg-Rillinger 2018,第130頁.
- ^ Haworth 1904,第473–474頁.
- ^ Hassall 1896,第342–343頁.
- ^ MacDonogh 2000,第373–374頁; Ritter 1936,第196–197頁.
- ^ MacDonogh 2000,第373–374頁; Schieder 1983,第175–176頁.
- ^ Asprey 1986,第620–621頁; MacDonogh 2000,第373–374頁; Ritter 1936,第196–197頁.
- ^ Kugler 1840,第556頁; Ritter 1936,第196–197頁.
- ^ Ritter 1936,第196–197頁.
- ^ Blanning 2016,第339頁.
- ^ (美)威爾·杜蘭著、幼獅文化公司譯,《世界文明史‧第十卷‧盧梭與大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447
- ^ St. Hedwig's Cathedral 2019: Die Hedwigskirche...war die erste katholische Kirche, die in der Residenzstadt Friedrichs des Großen nach der Reformation gebaut werden durfte...Der Bau geschah auf Wunsch der katholischen Gemeinde und mit der Zustimmung Friedrichs des Großen. [「海德維希教堂……是宗教改革後第一座被允許建於腓特烈大帝首都的天主教堂……其建造是依照天主教社群的請求,並經腓特烈大帝的批准。」]
- ^ Bonney & Trim 2006,第154頁; Fraser 2001,第58頁; MacDonogh 2000,第241頁.
- ^ Mitford 1970,第75頁.
- ^ Frederick II 1750b.
- ^ Kloes 2016,第102–108頁.
- ^ Holborn 1982,第274頁.
- ^ MacDonogh 2000,第364–366頁.
- ^ Fraser 2001,第241頁.
- ^ MacDonogh 2000,第363頁.
- ^ Brunhouse 2006,第419頁.
- ^ Ritter 1936,第180頁.
- ^ MacDonogh 2000,第347頁.
- ^ Fay 1945,第528頁.
- ^ Philippson 1905,第227–228頁.
- ^ Waite 1921,第306頁.
- ^ Kugler 1840,第124頁.
- ^ Melton2001,第267頁.
- ^ Gaffney 2020.
- ^ Barruel 1799,第1頁.
- ^ Luvaas, Jay. Napoleon On the Art of War. Simon and Schuster. 2001: 37. ISBN 978-0684872711.
參考文獻
[编辑]-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des Preußenkönigs., ISBN 3-88851-167-4
-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ße –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ISBN 3-548-26534-0
- Karl Otmar von Aretin (Mitverf.): Friedrich der Große. Herrscher zwischen Tradition und Fortschritt. ISBN 3-570-05104-8
- Oswald Hauser (Hrsg.): Friedrich der Große in seiner Zeit. ISBN 3-412-08186-8
- Johannes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ße. Der König und seine Zeit. Beck, München 2004, 624 S., ISBN 3-406-52209-2
- Ingrid Mittenzwei: 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Berlin, 1979
- Dieter Wunderlich: Vernetzte Karrieren. Friedrich der Große, Maria Theresia und Katharina die Große., ISBN 3-7917-1720-0
- S. Fischer-Fabian: Preußens Gloria
- Peter Lill: Friedrich der Große, Anekdoten. Ullstein Verlag 1991, ISBN 3-548-34865-3
- Christian Graf von Krockow: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Lebensbild. Verlag :Bastei Lübbe, ISBN 3-404-61460-7.
- Wolfgang Venohr: Der große König Verlag Gustav Lübbe 1995, ISBN 3-7857-0681-2
- Wolfgang Venohr: Fridericus Rex, Friedrich der Große-Porträt einer Doppelnatur Verlag Gustav Lübbe 1985 und 2000, ISBN 3-7857-2026-2
- 顧劍 《普魯士腓特烈大帝的生平戰役》
- Dennis Showalter "The War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1996年英文版
- Christopher Duffy "Frederick the Great: A Military Life" 1985年英文版
- Theodore Dodge "Great Captains" 1889年英文版
- 富勒 《西洋世界軍事史》 1981年中文版
腓特烈二世 (普鲁士) 出生于:1712年1月24日逝世於:1786年8月17日
| ||
|---|---|---|
| 統治者頭銜 | ||
| 前任者: 腓特烈·威廉一世 |
普魯士國王 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 |
繼任者: 腓特烈·威廉二世 |
| 布蘭登堡選帝侯 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 | ||
| 明登、哈爾伯施塔特、 紐沙特與默爾斯親王 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 | ||
| 前任者: 卡爾·埃德查 |
東菲士蘭親王 1744年5月25日-1786年8月17日 | |
引用错误:页面中存在<ref group="lower-alpha">标签或{{efn}}模板,但没有找到相应的<references group="lower-alpha" />标签或{{notelist}}模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