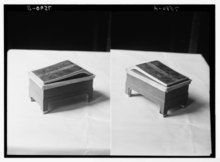比布魯斯王陵
| 比布魯斯王陵 | |
|---|---|
| مدافن جبيل الملكية | |
 | |
| 建立时间 | 公元前19世紀 |
| 建造目的 | 腓尼基比布魯斯王的安葬地 |
| 建筑风格 | 受古埃及影響的腓尼基風格 |
| 管理者 | 黎巴嫩文物總局[1] |
 | |
比布魯斯王陵是由九座青銅時代的地下豎井墓與墓室組成的墓葬群,內藏多位比布魯斯王的石棺。比布魯斯(今吉拜勒)是黎巴嫩的一座沿海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續有人居住城市之一。在青銅時代,該城與古埃及建立了重要的貿易聯繫,當地文化與葬俗因此深受埃及影響。古代比布魯斯的確切位置曾一度不為人知,直到19世紀末才由法國聖經學者與東方學家歐內斯特·勒南重新確認。古城遺址位於現代吉拜勒市區附近的一處丘陵上。其後,在法國託管當局的主持下,進行了小規模探溝發掘,並出土了刻有埃及象形文字的浮雕。這一發現引起了西方學界高度關注,進而促成了對該遺址的系統性勘查。
1922年2月16日,強降雨引發吉拜勒海邊懸崖滑坡,露出了一座地下墓室,其中安放著一具巨大的石棺。這座墓由法國的銘文學家兼考古學家夏爾·維羅洛奧進行初步探勘。隨後,法國埃及學家皮埃爾·蒙特在墓葬周邊展開大規模發掘,並陸續發現另外八座豎井墓與墓室。這些墓葬皆由一條垂直豎井通往底部的水平墓室所構成。蒙特將其劃分為兩組:第一組的墓葬可追溯至中期青銅時代(約公元前19世紀),其中部分未遭破壞,內含大量珍貴隨葬品,包括埃及中王國法老阿蒙涅姆赫特三世與阿蒙涅姆赫特四世的王室贈品、本地製作的埃及風格首飾,以及各類器皿用具。第二組墓葬則在古代即已遭盜掘,導致年代難以精確判定,但出土文物顯示,其中部分墓穴在晚期青銅時代(公元前16至11世紀)仍被使用。
除隨葬品外,共出土了七具石棺——那些未發現石棺的墓室,推測原本安置的是木棺,但已隨時間腐朽。這些石棺大多簡樸無飾,唯有阿希拉姆石棺例外。該石棺因刻有著名的腓尼基銘文而聞名,屬於比布魯斯王室銘文中的五篇之一,被視為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腓尼基字母實例。蒙特將比布魯斯墓葬的功能比擬為埃及的馬斯塔巴:當時人們相信,亡者的靈魂會從墓室經由豎井升向地表,抵達地面上的祭祀小堂,由祭司進行儀式。
歷史背景
[编辑]
比布魯斯(吉拜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續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在歷史上,它曾有多種稱呼:在古埃及語的象形文字記錄中,第四王朝時期稱為 Kebny;在阿卡德語的楔形文字阿馬爾奈文書中,即第十八王朝時期的埃及檔案裡,又被記作 Gubla(𒁺𒆷)。[2][3][4] 到了公元前二千紀,它的名字也出現在腓尼基語銘文中,例如阿希拉姆石棺的銘刻寫作 Gebal(𐤂𐤁𐤋)。[5][6][7] 其詞源來自(𐤂𐤁,意為「水井」)與(𐤀𐤋,意為「神」),可理解為「神之井」。[8] 另一種解釋則認為 Gebal 意為「山中的城鎮」,源自迦南語支的 Gubal。[9] 「Byblos」是後來出現的希臘外名,可能由 Gebal 音訛而來。[9] 古代聚落建於臨海高地,自公元前7000至8000年起便持續有人居住。[10] 在比布魯斯的考古層中,出土了屬於銅石並用時代的簡單圓形與長方形居住單位,以及甕棺葬遺跡。進入青銅時代後,比布魯斯逐漸發展為與美索不達米亞、安那托利亞、克里特及古埃及進行貿易的重要中心。[11][12]
埃及因需要黎巴嫩山脈盛產的木材,而積極維繫與比布魯斯的關係。[11][13][14] 在古王國時期(約公元前2686年至前2181年),比布魯斯屬於埃及的勢力範圍。約公元前2150年,隨著古王國滅亡所造成的權力真空,這座城市遭亞摩利人摧毀。[11][12] 不過,隨著埃及中王國(約公元前1991年至前1778年)的興起,比布魯斯的城牆與神廟獲得重建,並再次與埃及建立聯盟。[11][12] 至公元前1725年,中王國瓦解,埃及的尼羅河三角洲以及腓尼基沿岸城市落入喜克索斯人之手。一個半世紀後,埃及將喜克索斯人逐出,重新將腓尼基納入勢力範圍,並成功抵禦了米坦尼與赫梯的入侵。[11][12] 在這段時期,比布魯斯人[a]的貿易相當繁榮,並在當地出現了第一套拼音腓尼基字母。[12] 它由22個子音字母組成,簡明到足以供一般商人使用。[12][17][18]
14世紀中葉,比布魯斯與埃及的關係再次惡化,這可從比布魯斯國王里布哈達與埃及往來的《阿马尔奈文书》中得到印證。信件揭示,埃及已無力保護比布魯斯及其領土免受赫梯侵襲。[11][12][19] 在拉美西斯二世時期,埃及霸權曾短暫恢復,但不久之後,約公元前1195年,比布魯斯又遭海上民族摧毀。此時埃及國勢已衰,腓尼基因此迎來一段繁榮與獨立期。《威納蒙記》作為該時期的文獻,顯示比布魯斯君主與埃及仍有往來,但關係已趨冷淡。[11]
長期的埃及聯繫深刻影響了當地文化與喪葬習俗。正是在埃及統治時期,受埃及啟發的豎井墓制度開始出現。[20]
發掘歷史
[编辑]尋找古城
[编辑]
古代文獻與手稿曾提及「Gebal」的所在,但其具體位置在歷史上已失傳,直到19世紀中葉才重新被確認。 1860年,法國聖經學者兼東方學家歐內斯特·勒南在參與法國對黎巴嫩與敘利亞的遠征期間展開考古調查。他在尋找古城時參考了古希臘歷史學家兼地理學家斯特拉波的著作。斯特拉波指出,比布魯斯是一座距離海邊不遠的丘陵城市。[b][23][21] 然而,這段描述誤導了包括勒南在內的學者。他起初認為古城位於鄰近的卡蘇巴(Qassouba/Kassouba),但最終判斷該丘陵過於狹小,難以容納一座大型古代城市。[24][25]
勒南後來正確推斷,古代比布魯斯應位於現代城市郊外、十字軍時期建造的比布魯斯城堡所在的環形丘陵上。他的推測依據是一枚羅馬帝國埃拉伽巴路斯時期硬幣的背面圖像,上面描繪了一座城市,下方有河流流過。[c][25][24] 勒南據此認為,圖像中的河流正是環繞城堡丘陵的溪流。他以城堡為起點挖掘兩條長探溝,並出土古代文物,從而證實吉拜勒與古代的 Gebal/Byblos 為同一城市。[23][25]
早期考古工作
[编辑]
在法國託管時期,黎凡特高級專員昂利·古羅將軍設立了黎巴嫩文物局,並任命法國考古學家約瑟夫·沙莫納爾為首任局長。1920年10月1日,沙莫納爾由法國銘文學家兼考古學家夏爾·維羅洛奧接任。該機構將吉拜勒的考古調查列為優先任務,原因是勒南此前已在當地發現古代遺跡。[26]
1921年3月16日,史特拉斯堡大學的埃及學教授皮埃爾·蒙特致信法國考古學家夏爾·克萊蒙-加諾,提到他自己在1919年吉拜勒考古任務中發現的刻有埃及銘文的浮雕。克萊蒙-加諾深受吸引,並親自資助對該遺址的系統性調查,認為那裡可能有一座埃及神廟。蒙特被選為發掘負責人,並於1921年10月17日抵達貝魯特。[27][28] 在法國託管當局主持下,吉拜勒的考古發掘於1921年10月20日正式展開,採取每年三個月為一季的制度。[29]
王陵的發現
[编辑]
1922年2月16日,強降雨引發吉拜勒海邊懸崖滑坡,露出一處人工開鑿的地下空穴。翌日,黎巴嫩山的行政顧問即通知文物局,並宣佈發現了一座古代地下墓室,其中放置著一具巨大且尚未開啟的石棺。[30][31] 為防止盜掘,吉拜勒的穆迪爾謝赫瓦迪·霍貝什(Sheikh Wadih Hobeiche)立即封鎖現場。[32] 維羅洛奧到達後,對墓穴進行清理並編目內容物;[31] 之後他持續監督發掘,並於1922年2月26日開啟了石棺。[33] 第二座墓穴(稱為「墓二」)於1923年10月由蒙特發現;[34] 這一發現促使當年晚些時候展開周邊地區的系統性調查。[35] 蒙特負責比布魯斯古城的發掘工作直至1924年,其間又揭露了七座墓穴,使墓葬總數達到九座。[11] 1925年,法國考古學家莫里斯·迪南接替蒙特,並在該遺址持續工作長達四十年。[11]
地點
[编辑]古代比布魯斯/Gebal(今名:吉拜勒/Gebeil)位於貝魯特以北33 km(21 mi)處。[36] 它坐落在城市中世紀中心以南的一處濱海岬角上,由兩座丘陵構成,中間被一條谷地分隔。該聚落由一口深22米(72英尺)的井提供淡水來源。[37] 比布魯斯的考古遺丘防禦性極強,兩側環繞著曾用於海上貿易的雙港口。[37] 比布魯斯王陵是一處呈半圓形的墓地,位於岬角頂部的一條山脊上,俯瞰城市的兩個港口,並坐落於古代比布魯斯城牆之內。[38][39]
描述
[编辑]
蒙特為王室墓穴編號,並將其分為兩組:第一組位於北側,包括墓一至墓四;這些墓年代較早,建造亦更為精細。其中墓三與墓四在古代已遭盜掘而被清空,另兩座則保持原狀。[40][41]
第二組墓穴位於墓地南側,包括墓五至墓九。墓五至墓八的建造品質低於北側墓穴,年代亦較晚,且開鑿於黏土而非岩石之中。[40][42] 唯有墓九仍保留了與早期墓葬相似的精細結構跡象。在該墓中發現的陶器殘片上,刻有「阿比舍穆」之名的埃及象形文字,顯示其建造年代更接近北側墓穴。南側墓穴在古代均遭盜掘。[40][41][43]
墓一與墓二
[编辑]墓一由一條寬約4米(13英尺)、深約12米(39英尺)的方形豎井構成,通往一間地下墓室,部分鑿於堅石之中,部分鑿於黏土層內。[d] 西側牆體(將其與臨海懸崖隔開)在1922年的滑坡中坍塌。然而隨葬品並未受影響;在墓室內,考古人員於潮濕黏土中發現數個陶罐,以及一具大型白色石灰岩石棺,其棺蓋上有三個凸耳,便於搬運。[44]

該石棺呈南北向安置。[45][32] 在墓一墓室的北牆上,高約1米(3.3英尺)處有一個岩鑿開口,正對著石棺。此開口通往一條高約1.8米(5.9英尺)、寬約1.2米(3.9英尺)至1.5米(4.9英尺)的走廊,連接至墓二豎井的南側。該走廊同時也與墓一豎井西北角開出的通道相接。位於墓一與墓二豎井之間的S形走廊,在其中段北側另開一個小洞,通向一個粗糙開鑿的圓形空穴,內含一座古老墓葬。[45]
一道粗糙建造的牆體將墓一的墓室與其豎井隔開。豎井被填滿石塊與灰漿。相同材料亦被用於在豎井周圍砌築一個平台,其上曾建有類似馬斯塔巴墓的建築。這座受埃及風格啟發的建築僅存遺跡,因其後被羅馬時期的浴場所取代。與墓一的豎井不同,墓二的豎井並未以石塊與灰漿封閉,而僅以泥土覆蓋。豎井口上方覆蓋著五至六層石塊構成的厚板,為一座建築提供基礎,但如今僅存少數石材。[46]
墓二的豎井比墓一淺,由一道單層石牆將其與墓室隔開。墓二在發現時並未保存任何棺槨。若干陶罐與其他器物陷於厚厚的黏土層中,其中部分因墓室天花板的石塊脫落而受損。墓二墓室的天花板中央高度約3.5米(11英尺),向北側牆逐漸傾斜,最低僅約1米(3.3英尺)。[47] 墓室中央發現四塊石頭,原用以支撐一具已經朽壞的木棺,隨葬的珍貴器物因而散落於黏土之中。[34]
蒙特證明,墓一與墓二在1922至1923年發現之前從未遭盜掘,這與其前任維羅洛奧的報告相反。[48] 維羅洛曾在墓一墓室牆體中發現嵌入的玻璃碎片,並推測其年代屬於羅馬時期。[e][32]
墓三與墓四
[编辑]
墓三與墓四的豎井位於墓一與墓二以西,緊鄰羅馬浴場的北牆。墓三的豎井口約為2.5米 × 3.3米(8.2英尺 × 10.8英尺);其上覆蓋一層厚重的灰漿,其下是一層以灰封閉的石砌牆體,並在西南角附近垂直鑿有一條方形導管,寬約30 cm(12英寸),功能類似埃及馬斯塔巴墓中的serdab。另一條大小與形狀相近的導管穿過豎井較深的填充層,位於西北角,但僅延伸至約2米(6.6英尺)深。兩條導管並不相通。在豎井底部附近的北牆上還鑿有一處壁龕。[49][50]
墓三的墓室自豎井南牆向外延伸,由一道未用灰漿封固的單層石牆封閉。其結構精良,地面鋪石,牆壁垂直鑿至天花板。[51] 墓三未出現石棺;隨葬品散落於厚約70 cm(28英寸)的黏土層中。[52]
墓四位於墓三以東,深度僅約5.75米(18.9英尺),是整個墓地中最淺的一座。其豎井規模約為3.05米 × 3.95米(10.0英尺 × 13.0英尺);南側牆體覆蓋著厚約1米(3.3英尺)的石砌牆。墓室原本似乎未遭擾動,但考古人員發現其中的石灰岩石棺已被打開並清空。[53] 在墓四內亦發現了一條垂直導管,與墓三中的情況相似。[52] 這類導管似乎是比布魯斯喪葬祭儀的一個特色要素。[40] 墓四的石棺位於墓室中央,正對入口,與墓地其他墓穴所見的石棺安排相同。建造者在石棺底部放置了兩塊石頭,用以在傾斜的地面上支撐並保持水平。[53]
墓五(阿希拉姆王墓)
[编辑]墓五呈半圓形,是王陵中獨一無二的設計,被認為是阿希拉姆王的墓穴。其內部半填滿泥土,共置有三具石棺:靠牆的一具大型素面石棺、置於中央的雕刻精美的阿希拉姆石棺,以及一具較小的素面石棺。[55] 墓五同時也是唯一在豎井內發現銘文的墓葬。這段腓尼基銘文被稱為比布魯斯王陵塗鴉銘文,位於豎井南壁深約3米(9.8英尺)處,用以警告盜墓者不得入內。[56] 法國銘文學家勒內·迪索將其解讀為:「Avis, voici ta perte (est) ci-dessous」(「警告,你的毀滅就在下方」)。[57][58][59]
阿希拉姆墓的豎井位於北組墓穴(墓一至墓四)與南組墓穴(墓六至墓九)之間。豎井西側殘存有兩層石牆及柱基,屬於墓上方的建築結構。豎井上方土層極為緊實;在豎井東北角發現了一條長約2米(6.6英尺)的導管,與墓三、墓四的情況類似。豎井填土中混雜有模製碎片、大理石板及大量陶片,其樣式與其他墓穴中出土的陶器明顯不同。在豎井東、西兩壁分別於深約2.2米(7.2英尺)及4.35米(14.3英尺)處,各鑿出兩層方形槽孔,共四列,用以安放木製立柱,並在其上架設木板,形成橫跨豎井的樓層。[56] 蒙特認為,墓葬建造者認為僅憑豎井口的石板鋪蓋與半腰位置的封牆不足以保護國王的屍體,因此又加設木樑作為第三道障礙。盜墓者拆除了鋪板,並挖出木質結構;在清空豎井的過程中,他們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途中牆上的警告銘文。[59]
在木槽以下未發現更多陶片,但在接近墓室東側入口處,聚集了若干從墓室中拋出的雪花石膏瓶碎片。[59][60] 其中一片碎片上刻有拉美西斯二世的名字。考古人員發現封閉墓室的牆體部分坍塌,室內凌亂不堪,並半填滿泥漿。墓室中央的阿希拉姆雕刻石棺上方壓著一塊從穹頂墜落的巨大岩石。三具石棺全數遭盜掘,僅殘存人骨。[61]
墓六、墓七、墓八與墓九
[编辑]
這組墓穴位於墓地懸崖以東約50米(160英尺)處,距墓四豎井以南約30米(98英尺)。它們建於一處沉積層極厚的丘陵地帶。這些墓穴的豎井保存狀況較北側墓群差。墓八的豎井仍覆蓋著一層鋪地,而墓六與墓七的大部分地面覆蓋已經消失。墓六、墓七、墓八與墓九的墓室均完全掘於鬆軟黏土中。[63] 盜墓者能夠在柔軟的黏土間挖掘通道,從一座墓穴潛入另一座墓穴。[64]
墓六的豎井是整個墓地中最深的一座。其豎井由一堵方石牆體支撐至深約6米(20英尺)處;再往下則直接掘入黏土層,未再設石牆加固。[64] 與本組其他墓穴相同,墓六在古代即遭洗劫,僅在墓室內部及入口處留下少數器物殘件。該墓未發現任何石棺。[63]
墓七擁有規模最大的豎井,每邊約5米(16英尺)。其墓室的掘造方式與墓六相似,先穿過堅石再深入黏土層。發掘時,墓室已被黏土與礫石填滿約三分之二,一具石棺的弧形棺蓋突出於泥層之上。該石棺置於石鋪地層上,墓室牆壁則以保存狀況相對良好的石砌層加固。墓七的石棺形制簡單,長方形,外表粗糙;其凹形棺蓋兩端各伸出兩個大型凸耳,與墓一石棺相似,用於搬動沉重棺蓋。此墓中出土了相當數量的珍貴器物與首飾,似乎在古代盜掘時被遺漏。[65]
墓八的特徵在於豎井口呈菱形,在底部則趨於方形。分隔墓八與墓六的薄牆中央有一處穿孔,蒙特推測可能是因採石意外造成。豎井同樣深入堅石下方的黏土層,墓室發現時已被黏土與礫石填滿。墓室設有支撐牆,但大多已坍塌,地面覆滿小礫石。墓內發現一具簡單石棺、若干雪花石膏瓶碎片與其他陶器。除混雜於泥土中的少量金箔外,未出土其他珍貴器物。[66]
墓九的豎井貫穿約8米(26英尺)厚的岩層。封閉墓室的牆體並未被破壞,盜墓者是透過黏土層打通通道,進入墓五、墓八與墓九的墓室。墓九的屋頂已坍塌,墓室內完全被泥漿與天花板岩塊填滿。墓室地面鋪有石板,牆壁結構堅固且保存良好。盜墓者幾乎將墓中物品洗劫一空,僅剩雪花石膏、孔雀石與陶器殘片。發現物中包括數件刻有比布魯斯國王名字的陶器,其中王名為「Abi」(可能為縮寫)與「阿比舍穆」。[67]
- 蒙特繪製的王陵墓葬草圖
-
墓一與墓二的平面配置圖
-
墓一與墓二的剖面圖
-
墓三的平面與剖面圖
-
墓一、墓三與墓四的剖面圖
-
阿希拉姆王墓的平面圖與豎井剖面
-
墓四、墓七與墓八的平面與剖面圖
發現物
[编辑]石棺
[编辑]在比布魯斯王陵墓群中共出土七具石棺:墓一、墓四、墓七、墓八各有一具,而阿希拉姆王墓(墓五)內則有三具。[68][69] 其他墓室被認為原先安置有木棺,但已隨時間腐朽消失。[68][69] 墓二內確實曾有木棺,但已完全朽爛,只留下一批隨葬品散落於墓室地面。[70]
墓一與墓四出土的石棺皆採用來自鄰近黎巴嫩山脈的優質白色石灰岩製作;其棺壁厚實,打磨光滑,未施任何雕飾。[33] 此外,墓一、墓四、墓五與墓七的石棺在形制上相似,與埃及常見的石棺接近。不同之處在於,比布魯斯出土的石棺棺蓋保留了凸耳,便於工匠搬運。[71][45][32] 這些特徵,以及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造型相似的雪花石膏容器,顯示這些石棺可歸屬於一個較為集中的時期。[40]

墓一的石棺尺寸約為1.48米 × 2.82米(4.9英尺 × 9.3英尺),高度1.68米(5.5英尺)。[f][33] 棺身側壁厚約35 cm(14英寸),底部厚約44 cm(17英寸)。[32] 棺蓋邊緣經削角處理,下緣切削後能插入棺體數公分。棺蓋背面呈圓弧形,並雕有縱向不規則大小的凹槽紋。中央凹槽最寬,兩側依序排列五道逐漸變窄的凹槽。[72] 棺蓋靠近四角的位置斜伸出三個凸耳;西北角的凸耳及一角棺蓋已折斷並殘留在棺腳處。該石棺於1922年2月26日開啟。[33][73]
墓四的石棺尺寸約為1.41米 × 3米(4.6英尺 × 9.8英尺),高度1.49米(4.9英尺)。其棺身製作稍顯精細,兩側長邊在上下邊緣皆削成斜角;短邊底部則延伸出如長凳般的凸檯。蒙特確認該石棺原本並未配有石質棺蓋;他在棺身邊緣發現黑色痕跡,顯示其原本覆蓋著一具弧形木棺蓋。[74]
墓四、墓五與墓七的石棺皆於第五次考古發掘行動中出土,此次行動自1926年3月8日持續至同年6月26日。[75]
阿希拉姆王石棺
[编辑]阿希拉姆石棺由砂岩製成,出土於墓五。其名稱源於棺體上的淺浮雕雕刻,以及歸屬於阿希拉姆王的腓尼基銘文。該銘文共38字,是已知的五篇比布魯斯王室銘文之一。它以古腓尼基語方言書寫,被視為迄今發現的最早一例完整發展的腓尼基字母。[76] 對部分學者而言,阿希拉姆石棺銘文被認為界定了字母傳入歐洲的最早時間點。[76] 此石棺長約3米(9.8英尺)、寬1.14米(3.7英尺)、高1.47米(4.8英尺)(含棺蓋)。[77]
石棺棺身上緣環繞一圈倒置的蓮花飾帶,花朵在含苞與盛放之間交替排列。主體浮雕場景的上方以粗繩紋圖案框飾,石棺四角則雕有立柱作為裝飾。[78] 棺身底部由四隻獅子承托,四面皆有。獅子的頭部與前腿向外突出於棺槽之外,而身體其餘部分則以浮雕形式刻於石棺長邊。[78]

石棺正面的主場景描繪國王端坐於寶座上,手持一枝枯萎的蓮花。寶座前方是一張滿載供品的桌案,之後是七名男子組成的行列。[79] 石棺兩側各刻有一組四名女性的葬禮哀悼場景,其中兩人袒露胸膛,另兩人則以雙手拍擊頭部表示哀傷。[79] 石棺背面則描繪了一隊男女捧持供品的行列。[80]
石棺蓋呈輕微的弧形,與同墓群其他石棺相似。棺蓋兩端各有一個獅首形狀的凸耳,獅身則以浮雕形式刻於棺蓋平面。兩尊長約171 cm(5.61英尺)的鬍鬚人像分別雕刻於獅子兩側,其中一人手持枯萎蓮花,另一人手持盛開蓮花。蒙特認為這兩人皆代表亡王本人。[78] 黎巴嫩考古學家兼博物館館長莫里斯·謝哈布後來發現石棺上有紅色顏料痕跡,他則將這兩人解釋為亡王與其子。[81]
石棺銘文共38字,分為兩部分。[82][83] 較短的一段位於石棺本體,刻於蓮花飾帶上方的狹窄帶狀空間。[83] 較長的一段則刻於棺蓋前方長邊。[84] 銘文帶有警告性質,詛咒任何膽敢褻瀆墓葬之人。[85]
隨葬品
[编辑]
埃及王室饋贈
[编辑]墓一出土一件高約12 cm(4.7英寸)的黑曜石瓶與瓶蓋,鑲有金飾,並以象形文字刻有阿蒙涅姆赫特三世的即位名。[88] 同墓另出土兩件雪花石膏瓶。[89]
墓二出土兩件埃及王室饋贈。第一件為一具長約45 cm(18英寸)的長方形黑曜石箱與箱蓋,鑲有金飾。箱體立於四足之上,箱蓋上完整保存著埃及象形文字的象形繭,其中載有阿蒙涅姆赫特四世的即位名與尊號。[h][91] 該箱原本盛放何物尚不清楚;類似的器物常見於埃及墓葬浮雕中,被稱為「pr 'nti」,意即「香料之屋」。[90] 第二件饋贈為一件石瓶,上刻有阿蒙涅姆赫特四世的名字,其王名環記載:「善神萬歲,拉之子,阿蒙涅姆赫特,永生不息。」[90]
首飾與貴重器物
[编辑]墓葬中出土大量以金、銀與寶石製成的王室首飾,其中不少具有濃厚的埃及風格。墓一、墓二與墓三皆出土有雕鑿精細、帶有埃及風格的金製胸飾。墓二內更發現一件埃及風格、於本地製作的鑲寶金胸飾,連同其頸鏈,以及一枚貝殼形掐絲琺瑯吊墜,上刻有伊普-舍穆-阿比王的名字。墓一與墓二各出土一面大型銀質手鏡;三座墓內皆發現以金、紫水晶製成的手鐲與戒指、銀質涼鞋,以及以青銅與黃金製作、雕飾並刻銘的霍佩什彎刀。墓二出土的彎刀上刻有墓主伊普-舍穆-阿比王及其父阿比舍穆的名字。其他隨葬品還包括以烏銀鑲嵌工藝與黃金裝飾的銀刀、數件青銅三叉戟、工藝精美的茶壺狀銀瓶,以及各類金、銀、青銅、雪花石膏與陶製容器。[92][93]
墓一內另有一件罕見的出土品:一片銀質瓶殘片,上飾有螺旋紋樣。法國藝術史學者埃德蒙·波蒂耶將其與邁錫尼墓地A的墓四所出土的金製酒罐裝飾相提並論。[94] 此銀瓶顯示出愛琴藝術對比布魯斯本地藝術的影響,或可作為比布魯斯與邁錫尼存在貿易往來的證據。[93][94]
年代
[编辑]法國神父兼考古學家路易-于格·文森、皮埃爾·蒙泰,以及其他早期學者根據彩繪陶片的特徵,認為這些墓葬屬於青銅時代中、晚期的比布魯斯諸王。[95]
墓一、墓二與墓三
[编辑]依據維羅洛奧與蒙泰的看法,規模宏大的墓一、墓二與墓三可追溯至青銅時代中期,特別是古埃及中王國的埃及第十二王朝(前19世紀)。蒙泰的斷代主要根據墓中出土的隨葬品與埃及王室饋贈:墓一中發現一件刻有阿蒙涅姆哈特三世名號的香膏瓶,而墓二則出土一件黑曜石箱,其上刻有其子兼繼承人阿蒙涅姆哈特四世的名字。[96][97]
墓五至墓九
[编辑]蒙泰將他在墓五豎井中發現的陶片風格,與英國埃及學家弗林德斯·皮特里於阿瑪納(阿肯那頓王宮遺址)出土的陶瓶進行比較。兩者皆有寬大的棕色或黑色彩繪帶,將容器本體分成若干區塊,每一區內飾有豎線與圓形圖案,小陶瓶把手的形制亦完全一致。這些相似性使蒙泰推斷,這些比布魯斯陶片與埃及新王國時期(約前1550年-約前1077年)為同時代製品。[98][99]
第二組墓葬(墓六至墓九)在古代均已遭盜掘,因此難以準確斷代。不過,部分跡象顯示其年代可能介於中青銅時代晚期至晚青銅時代之間。[100][99]
歸屬
[编辑]
學者們依循法國藝術史專家埃德蒙·波蒂耶的觀察,注意到墓一中發現的螺旋紋裝飾,與邁錫尼墓四出土的金製彩陶酒罈上的圖案極為相似。[比較]
部分石棺主人的名字已從考古發現中得知。墓一屬於亞比謝穆王(Abishemu,亦作「Abishemou」或「Abichemou」),他曾接受法老阿蒙涅姆哈特三世的饋贈;墓二則屬於其子伊普-謝穆-阿比(Ip-Shemu-Abi,亦作「Ypchemouabi」),他同樣接受了阿蒙涅姆哈特四世之子的饋贈。這些禮品顯示,亞比謝穆與伊普-謝穆-阿比的在位時間,應與埃及第十二王朝晚期諸王同時代。[34][102][103]
伊普-謝穆-阿比與其父亞比謝穆的名字,都被刻在墓二發現的霍佩什彎刀柄上。[104] 墓一墓室與墓二豎井之間有一條通道相連;蒙泰推測,這是伊普-謝穆-阿比特意挖掘,以便能與其父「永遠保持聯繫」。[105]
蒙泰推測,墓四是為一位具有埃及血統的附庸王所建,他認為該王是由埃及任命的,因而中斷了原有的傑貝勒王室世系。這一理論主要依據蒙泰在墓中發現的一枚刻有埃及名字「梅傑德-特比特-阿特夫」(Medjed-Tebit-Atef)的聖甲蟲印章。[102][106]
墓五的石棺屬於亞希拉姆王(Ahiram);[71] 其華麗的裝飾與浮雕使之有別於其他石棺。亞希拉姆石棺出土於墓五墓室,與另外兩具簡樸石棺並列。石棺蓋上刻有死者與其繼任者的肖像,而石棺的葬禮銘文則記載了逝世國王的姓名,以及其子兼繼任者皮爾西巴爾(Pilsibaal)的名字。[i][81][109]
墓九出土的陶器殘片上刻有亞比謝穆之名,且使用埃及象形文字。[41] 這使學者們將該墓石棺歸屬於「亞比謝穆二世」,即年長亞比謝穆的孫子。此推測基於腓尼基人的習俗,即以祖父的名字為王子命名。[110]
功能
[编辑]蒙泰將比布魯斯的墓葬比作埃及的「馬斯塔巴」(mastaba),並解釋說,在古埃及的葬禮文獻中,亡者的靈魂被認為會從墓室飛出,經由葬坑通道,抵達地面上的禮拜堂,由祭司在那裡主持儀式。[111]
他又將墓一與墓二之間的連通隧道,比作與法老佩皮二世(Pepi II)同時代的高官、扎烏之子阿巴(Aba)的墓葬。阿巴與父親同葬於代爾加布拉維的同一墓穴中。阿巴在銘文中記錄自己選擇與父親同穴安葬的理由:「因此,我確保自己與這位扎烏葬於同一墓中,為了能與他同處一地。並非因為我沒有能力修建另一座墓,而是為了每日能見到這位扎烏,為了能與他同處一地。」[111]
注釋
[编辑]- ^ 古代文獻中以 Gebalite 或 Giblite 稱呼「Gebal」的居民,即腓尼基語中的城市名,也是現代名稱「吉拜勒」的來源。[15][16] 本文採用「比布魯斯人」作為住民稱呼,因所述時期屬於腓尼基時代,早於希臘外名「Byblos」。
- ^ 「如今,比布魯斯——昔日西尼拉斯的王宮所在地——被奉為阿多尼斯的聖地;但龐培曾以斧斬首其僭主,使之擺脫暴政。該城位於一處高地,距海僅有短短距離。」[22]
- ^ "R. IERAC BYBLOY. Femme tourrelée et voilée, assise dans un temple tétrastyle; au-dessous d'elle, un fleuve vu à mis-corps..." [背面:IERAC BYBLOY。戴城垛冠與面紗的女子端坐於四柱神殿;其下方有一條側身描繪的河流][24]
- ^ 此半島區域的岩層距現今地表約4米(13英尺)至5米(16英尺),厚度僅6米。當時的工匠自側面鑿穿該岩層,認為深度不足,便繼續往黏土層內掘進。[44]
- ^ "II semble bien que personne n'ait tenté de soulever le couvercle du sarcophage. Cependant quelqu'un est entré dans la grotte, à l'époque romaine sans doute, puis qu'on a trouvé mêlés aux pierres du mur de soutènement des fragments de verre qui datent sûrement de ce temps-là."(似乎沒有人試圖掀開石棺的蓋子。然而,在羅馬時代很可能有人進入過墓穴,因為在支撐牆的石塊中發現了玻璃碎片,顯然屬於那個時期。)[32]
- ^ 含棺蓋總高約2.32米(7.6英尺)[32]
- ^ 王陵隨葬器物在蒙特的《圖譜》中編號自610至872。[86]
- ^ "Vive le dieu bon, maître des Deux Terres, roi de la Haute et Basse Égypte, Ma'a-kherou-rê, aimé de Tourn, seigneur d'Héliopolis (On), à qui est donnée la vie éternelle comme Râ."(「善神萬歲,兩地之主,上下埃及之王瑪阿克魯拉,圖恩所愛,赫利奧波利斯之主,受賜永生如同拉神。」)[90]
- ^ 亞希拉姆之子的名字曾因銘文中出現的缺字而長期存在爭議。自1924年亞希拉姆石棺銘文首次發表以來,「伊托巴爾」(Ittobaal)的讀法一直佔主流。然而,新的銘文學研究已證明此解讀不可能成立,並透過現代古文字學與書法學的方法提出新重建,確認亞希拉姆之子的名字應為「普爾西巴爾」(Pulsibaal)或「皮爾西巴爾」(Pilsibaal)。[107][108]
參考資料
[编辑]文獻
[编辑]- ^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2009.
- ^ Cooper 2020,第298頁.
- ^ Wilkinson 2011,第66頁.
- ^ Moran 1992,第143頁.
- ^ Head et al. 1911,第763頁.
- ^ Huss 1985,第561頁.
- ^ Lehmann 2008,第120, 121, 154, 163–164頁.
- ^ Salameh 2017,第353頁.
- ^ 9.0 9.1 Harper 2000.
- ^ DeVries 2006,第135頁.
-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DeVries 1990,第124頁.
- ^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Awada Jalu 1995,第37頁.
- ^ Redford 2021,第89, 296頁.
- ^ Jidejian 1986,第1頁.
- ^ Head et al. 1911,第791頁.
- ^ Barry 2016,headword: Gebal.
- ^ Fischer 2003,第90頁.
- ^ Segert 1997,第58頁.
- ^ Moran 1992,第197頁.
- ^ Charaf 2014,第442頁.
- ^ 21.0 21.1 Renan 1864,第173頁.
- ^ Strabo 1930,第263頁,§16.2.18.
- ^ 23.0 23.1 Montet 1928,第2–3頁.
- ^ 24.0 24.1 24.2 Mionnet 1806,第355–356頁.
- ^ 25.0 25.1 25.2 Renan 1864,第173–175頁.
- ^ Dussaud 1956,第9頁.
- ^ D. 1921,第333–334頁.
- ^ Montet 1921,第158–168頁.
- ^ Vincent 1925,第163頁.
- ^ Virolleaud 1922,第1頁.
- ^ 31.0 31.1 Dussaud 1956,第10頁.
- ^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Virolleaud 1922,第275頁.
- ^ 33.0 33.1 33.2 33.3 Montet 1928,第153–154頁.
- ^ 34.0 34.1 34.2 Montet 1928,第145–147頁.
- ^ Vincent 1925,第178頁.
- ^ Sparks 2017,第249頁.
- ^ 37.0 37.1 Lendering 2020.
- ^ Montet 1928,第22–23, 143頁.
- ^ Nigro 2020,第67頁.
- ^ 40.0 40.1 40.2 40.3 40.4 Porada 1973,第356頁.
- ^ 41.0 41.1 41.2 Montet 1928,第212頁.
- ^ Montet 1928,第214頁.
- ^ Montet 1928,第155頁.
- ^ 44.0 44.1 Montet 1928,第143頁.
- ^ 45.0 45.1 45.2 Montet 1928,第144頁.
- ^ Montet 1928,第144–145頁.
- ^ Montet 1928,第145–146頁.
- ^ Montet 1928,第146頁.
- ^ Montet 1928,第148–150頁.
- ^ Montet 1929,第Pl. LXXVI (illustration)頁.
- ^ Montet 1928,第150頁.
- ^ 52.0 52.1 Montet 1928,第151頁.
- ^ 53.0 53.1 Montet 1928,第152–153頁.
- ^ Vincent 1925,PLANCHE VIII.
- ^ Porada 1973,第356–357頁.
- ^ 56.0 56.1 Montet 1928,第215–216頁.
- ^ Dussaud 1924,第143頁.
- ^ Vincent 1925,第189頁.
- ^ 59.0 59.1 59.2 Montet 1928,第217頁.
- ^ Porada 1973,第357頁.
- ^ Montet 1928,第217, 225頁.
- ^ Dunand 1937,XXVIII.
- ^ 63.0 63.1 Montet 1928,第205–206頁.
- ^ 64.0 64.1 Montet 1928,第205頁.
- ^ Montet 1928,第207–210頁.
- ^ Montet 1928,第210頁.
- ^ Montet 1928,第210–213頁.
- ^ 68.0 68.1 Montet 1929,第118–120頁.
- ^ 69.0 69.1 Montet 1928,第144, 146, 151–153, 205–220, 229頁.
- ^ Montet 1928,第146–147頁.
- ^ 71.0 71.1 Porada 1973,第355頁.
- ^ Virolleaud 1922,第276頁.
- ^ Virolleaud 1922,第275–276頁.
- ^ Montet 1928,第154頁.
- ^ Dunand 1939,第2頁.
- ^ 76.0 76.1 Cook 1994,第1頁.
- ^ Maïla Afeiche 2019.
- ^ 78.0 78.1 78.2 Montet 1928,第229頁.
- ^ 79.0 79.1 Montet 1928,第230頁.
- ^ Montet 1928,第231頁.
- ^ 81.0 81.1 Porada 1973,第359頁.
- ^ Lehmann 2008,第121–122頁.
- ^ 83.0 83.1 Montet 1928,第236頁.
- ^ Montet 1928,第237頁.
- ^ Teixidor 1987,第137頁.
- ^ Montet 1929,第4–6頁.
- ^ Montet 1928,第202頁.
- ^ Montet 1928,第155–156頁.
- ^ Montet 1928,第156–159頁.
- ^ 90.0 90.1 90.2 Montet 1928,第159頁.
- ^ Montet 1928,第157–159頁.
- ^ Montet 1928,第155–204頁.
- ^ 93.0 93.1 Dussaud 1930,第176–178頁.
- ^ 94.0 94.1 Pottier 1922,第298–299頁.
- ^ Montet 1928,第129, 219頁.
- ^ Virolleaud 1922,第273–290頁.
- ^ Montet 1928,第16–17, 25, 219頁.
- ^ Montet 1928,第220頁.
- ^ 99.0 99.1 Kilani 2019,第97頁.
- ^ Montet 1928,第213–214頁.
- ^ Montet 1929,PLANCHE CXI.
- ^ 102.0 102.1 Dussaud 1930,第176頁.
- ^ Montet 1927,第86頁.
- ^ Montet 1928,第174頁.
- ^ Montet 1928,第147頁.
- ^ Montet 1928,第203頁.
- ^ Lehmann 2005,第38頁.
- ^ Lehmann 2015,第178頁.
- ^ Lehmann 2008,第164頁.
- ^ Helck 1971,第67頁.
- ^ 111.0 111.1 Montet 1928,第147–148頁.
書目
[编辑]- Awada Jalu, Sawsan. The stones of Byblos (PDF). UNESCO Courier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95: 34–37 [2022-03-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1-10-08).
- Barry, John D. The Lexham Bible Dictionary. Bellingham, Washington: Faithlife Corporation. 2016 (英语).
- Chanteau, Julien; Zaven, Tania. Byblos excavations, yesterday and today. National Museum of Antiquities (The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Culture/Directorate General of Antiquities (Lebanon) (编). Byblos: A Legacy Unearthed. Leiden: Sidestone Press. 2024: 17–25. ISBN 9789464262209.
- Charaf, Hanan. The northern Levant (Lebanon)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Steiner, Margreet L.; Killebrew, Ann E. (编).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 8000–332 B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ISBN 9780191662553. OCLC 1164893708 (英语).
- Cook, Edward M. On the Linguistic Dating of the Phoenician Ahiram Inscription (KAI 1)
 .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53 (1): 33–36. ISSN 0022-2968. JSTOR 545356. S2CID 162039939. doi:10.1086/373654.
.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53 (1): 33–36. ISSN 0022-2968. JSTOR 545356. S2CID 162039939. doi:10.1086/373654. - Cooper, Julien. Toponymy on the Periphery: Placenames of the Eastern Desert, Red Sea, and South Sinai in Egyptian Documents from the Early Dynastic until the End of the New Kingdom. Leiden: BRILL. 2020. ISBN 9789004422216. OCLC 1240671488 (英语).
- D., R. Mission Pierre Montet à Byblos [Pierre Montet's mission in Byblos].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21, 2 (4): 333–334. ISSN 0039-7946. JSTOR 4389726 (法语).
- DeVries, LaMoine F. Mills, Watson E.; Bullard, Roger Aubrey; McKnight, Edgar V. , 编. Mercer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Macon, Georgia: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9780865543737. OCLC 613917443 (英语).
- DeVries, LaMoine F. Cities of the Biblical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chaeology,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Biblical Sites. Eugene, Oreg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6. ISBN 9781556351204. OCLC 1026419222 (英语).
- Dunand, Maurice. Fouilles de Byblos, Tome 1er, 1926–1932 (Atlas) [The Byblos excavations, Tome 1, 1926–1932 (Atlas)].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24. Paris: Libra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7. OCLC 85977250 (法语).
- Dunand, Maurice. Fouilles de Byblos: Tome 1er, 1926–1932 [The Byblos excavations, Tome 1, 1926–1932].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24. Paris: Libra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39. OCLC 35255029 (法语).
- Dussaud, René. Les inscriptions phéniciennes du tombeau d'Ahiram, roi de Byblos [Phoenician inscriptions from the Tomb of Ahiram, King of Byblos].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24, 5 (2): 135–157. OCLC 977806804. doi:10.3406/syria.1924.3038 (法语).
- Dussaud, René. Les quatre campagnes de fouilles de M. Pierre Montet a Byblos [The four excavation campaigns of Mr. Pierre Montet at Byblos]
 .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30, 11 (2): 164–187. ISSN 0039-7946. JSTOR 4237002. OCLC 754446601. doi:10.3406/syria.1930.3470 (法语).
.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30, 11 (2): 164–187. ISSN 0039-7946. JSTOR 4237002. OCLC 754446601. doi:10.3406/syria.1930.3470 (法语). - Dussaud, René. L'oeuvre scientifique syrienne de M.Charles Virolleaud [the Syrian scientific work of M Charles Virolleaud].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56, 33 (1): 8–12. OCLC 754457329. doi:10.3406/syria.1956.5186 (法语).
- Fischer, Steven Roger. History of Writing.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3. ISBN 9781861891679. OCLC 439272651 (英语).
- Harper, Douglas. Etymology of Byblos.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Tupalo, Mississippi: Douglas Harper. 2000 [2022-03-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3).
- Head, Barclay Vincent; Hill, Sir George Francis; MacDonald, George; Wroth, Warwick William. Historia Numorum: A Manual of Greek Numisma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 ISBN 9780722221877. OCLC 1083895850 (英语).
- Helck, Wolfgang. Die Beziehungen Ägyptens zu Vorderasien im 3. und 2. Jahrtausend v.Chr.: 2., verbesserte Auflage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the Middle East in the 3rd and 2nd millennium BC]. Ägyptologische Abhandlungen.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71. ISBN 9783447012980. OCLC 1049030285 (德语).
- Huss, Werner. Geschichte der Karthager [History of the Carthaginians]. Munich: C.H. Beck. 1985: 561. ISBN 9783406306549. OCLC 887765515 (德语).
- Jidejian, Nina. Byblos through the ages. Beirut: Dar el-Machreq Publishers. 1986. OCLC 913477845.
- Kilani, Marwan. Byblos in the Late Bronze Ag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Levantine and Egyptian Worlds. Leiden: BRILL. 2019. ISBN 9789004416604. OCLC 8303726422 (英语).
- Kilani, Marwan. Byblos and its architecture during the late bronze age. National Museum of Antiquities (The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Culture/Directorate General of Antiquities (Lebanon) (编). Byblos: A Legacy Unearthed. Leiden: Sidestone Press. 2024: 189–193. ISBN 9789464262209.
- Lehmann, Reinhard G. Die Inschrift(en) des Ahirom-Sarkophags und die Schachtinschrift des Grabes V in Jbeil (Byblos)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Ahirom sarcophagus and the shaft inscription of Tomb V in Jbeil (Byblos)]. Mainz am Rhein: von Zabern. 2005. ISBN 9783805335089. OCLC 76773474 (德语).
- Lehmann, Reinhard G. Calligraphy and Craftsmanship in the Ahirom inscription. Considerations on skilled linear flat writing in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yblos. MAARAV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Western Academic Press). 2008, 15 (2): 119–164. S2CID 257837024. doi:10.1086/MAR200815202.
- Lehmann, Reinhard G. Wer war Aḥīrōms Sohn (KAI 1:1)? Eine kalligraphisch-prosopographische Annäherung an eine epigraphisch offene Frage [Who was Aḥīrōm's son (KAI 1:1)? A calligraphic-prosopographic approach to an epigraphically open question]. Fünftes Treffen der Arbeitsgemeinschaft Semitistik in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University of Basel. 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 425. Münster: Ugarit-Verlag: 163–180. February 2015. OCLC 918796397.
- Lendering, Jona. Byblos. Livius. 2020 [2021-07-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6-02).
- Maïla Afeiche, Anne-Marie. Le sarcophage d'Ahiram roi de Byblos [The sarcophagus of Ahiram, king of Byblos]. Agenda Culturel. Beirut. 2019-09-24 [2022-05-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06).
- Mionnet, Théodore Edme. Description de médailles antiques, grecques et romaines; avec leur degré de rareté et leur estimation; ouvrage servant de catalogue à une suite de plus de vingt mille empreintes en soufre, prise sur les pièces originales [Description of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coins; with their degree of rarity and their estimate; work serving as a catalog to a suite of more than twenty thousand prints in sulfur, taken on the original pieces]. Paris: Imprimerie de Testu. 1806. OCLC 632656145 (法语).
- Montet, Pierre. Lettre à M. Clermont-Ganneau [Letter to Mr. Clermont-Ganneau].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Paris: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des Belles Lettres). 1921, 65 (2): 158–168. ISSN 0065-0536. doi:10.3406/crai.1921.74450. 4649740372 (法语).
- Montet, Pierre. Un Egyptien, roi de Byblos, sous la XIIe dynastíe Étude sur deux scarabées de la collection de Clercq [An Egyptian king of Byblos under the Twelfth Dynasty, study on two scarabs from the Clercq collection]
 .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27, 8 (2): 85–92. ISSN 0039-7946. JSTOR 4195343. doi:10.3406/syria.1927.3277 (法语).
.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27, 8 (2): 85–92. ISSN 0039-7946. JSTOR 4195343. doi:10.3406/syria.1927.3277 (法语). - Montet, Pierre. Byblos et l'Egypte: Quatre Campagnes de Fouilles à Gebeil 1921–1922–1923–1924 (Texte) [Byblos and Egypt: four excavation campaigns in Gebeil 1921–1922–1923–1924 (Text)].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11. Paris: Geuthner. 1928. OCLC 1071294753 (法语).
- Montet, Pierre. Byblos et l'Egypte Quatre Campagnes de Fouilles à Gebeil 1921–1922–1923–1924 (Atlas) [Byblos and Egypt: four excavation campaigns in Gebeil 1921–1922–1923–1924 (Atlas)]. Bibliothèque archéologique et historique 11. Paris: Geuthner. 1929. OCLC 904661212 (法语).
- Moran, William L.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ISBN 9780801842511. OCLC 797943180 (英语).
- Nigro, Lorenzo. Byblos, an ancient capital of the Levant. La Revue Phénicienne (Beirut). 2020, (Spécial 100 ans): 61–74.
- Porada, Edith. Notes on the Sarcophagus of Ahiram. Journal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ern Society (New York: 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 1973, 5 (1): 355–372. OCLC 602273437 (英语).
- Pottier, Edmond. Observations sur quelques objets trouvés dans le sarcophage de Byblos. Lettre à M. René Dussaud, Directeur de la revue Syria [Observations on some objects found in the sarcophagus of Byblos. Letter to Mr. René Dussaud, Director of the review Syria].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22, 3 (4): 298–306. ISSN 0039-7946. doi:10.3406/syria.1922.8854 (法语).
- Redford, Donald B.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ISBN 9780691214658. OCLC 1241099443 (英语).
- Renan, Ernest. Mission de Phénicie Dirigée par M. Ernest Renan [Mission to Phoenicia, directed by Mr. Ernest Rena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1864. OCLC 763570479 (法语).
- Salameh, Franck. The other Middle East: An anthology of modern Levantine litera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ISBN 9780300204445. OCLC 1065338550 (英语).
- Segert, Stanislav. Kaye, Alan S.; Daniels, Peter T , 编. Phonologies of Asia and Africa - including the Caucasus.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1997. ISBN 9781575060194. OCLC 929631154 (英语).
- Sparks, Rachael Thyrza. Stone Vessels in the Levant. Oxford: Routledge. 2017-07-05. ISBN 9781351547789. OCLC 994205911 (英语).
- Strabo. Geography, Volume VII: Books 15–16. Translated by Horace Leonard Jon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4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263 [2022-07-06]. OCLC 899735754.
- Teixidor, Javier. L' inscription d'Ahiram à nouveau [The Ahiram inscription revisited].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87, 64 (1): 137–140. OCLC 754460302. doi:10.3406/syria.1987.6979 (法语).
-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Byblo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re. Paris: UNESCO World Heritage Center. 2009 [2022-06-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09) (英语).
- Vincent, Louis-Hugues. Les fouilles de Byblos [The excavations of Byblos]. Revue Biblique (Louvain: Peeters Publishers). 1925, 34 (2): 161–193. ISSN 1240-3032. JSTOR 44102762. OCLC 718118625 (法语).
- Virolleaud, Charles. Découverte à Byblos d'un hypogée de la douzième dynastie égyptienne [Discovery in Byblos of a Hypogeum of the Egyptian Twelfth Dynasty]
 .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22, 3 (4): 273–290. ISSN 0039-7946. JSTOR 4195157. OCLC 1136131170. doi:10.3406/syria.1922.8851 (法语).
. Syria (Beirut: Institut français du Proche-Orient). 1922, 3 (4): 273–290. ISSN 0039-7946. JSTOR 4195157. OCLC 1136131170. doi:10.3406/syria.1922.8851 (法语). - Wilkinson, Toby. The Rise and Fall of Ancient Egypt. New York: A&C Black. 2011. ISBN 9780679604297. OCLC 710823381.